新冠病毒來源于哪里?是自然產生還是人為制造?
這是事關全球抗疫大局的嚴肅科學問題。然而我們遺憾地看到,一些政界人士和媒體正在無視科學精神,故意炒作病毒來源問題,也把攻擊的矛頭對準了專業的科研機構。
7月16日,21位中國科學家和1位在中國工作的英國學者聯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(《中國科學:生命科學》英文版)發表題為“On the origin of SARS-CoV-2—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”的觀點文章,運用經典進化理論——“盲眼鐘表匠”,有力論證了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來源于自然,而不可能由人為制造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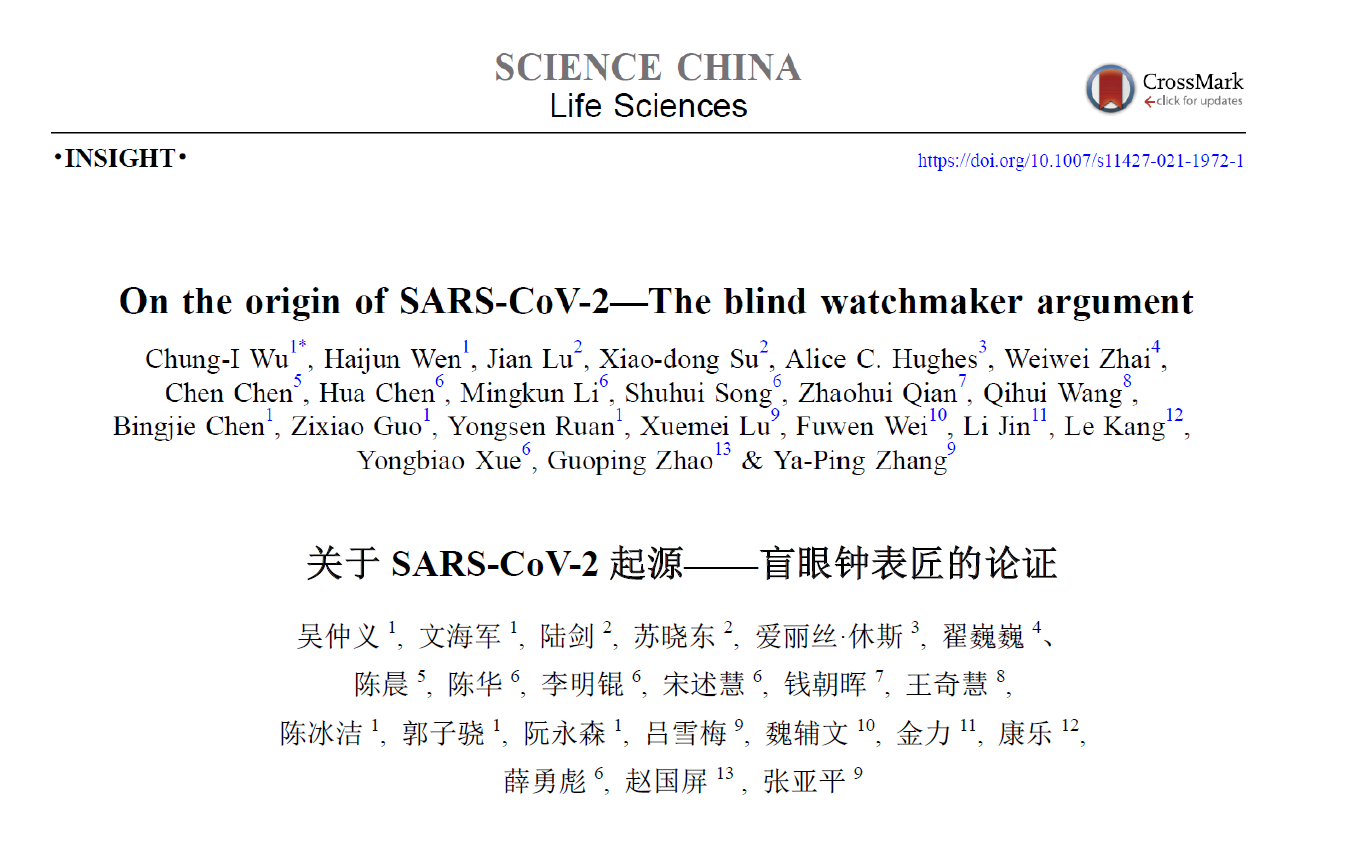
《中國科學報》專訪了論文第一作者兼通訊作者,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、臺灣“中研院”院士吳仲義。
他在采訪中表示,關于疫情溯源,中國科學家已經提出了一系列模型和假說,也期待國際同行拿出科學的態度,客觀討論、集思廣益,找到一條通往真相的路。
“21世紀以來,我們已經遭遇了3次冠狀病毒引發的疫情。所以我們最好搞清楚,它們到底從何而來。這事關全人類的命運。”吳仲義說。
《中國科學報》:在當前的大環境下,您與眾多科學家聯名發表這篇論文,是出于怎樣的想法?
吳仲義:這次全球疫情之所以失控,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科學與科學家的聲音太過微弱。如果全球能以科學的態度積極應對,原本去年5月就可能結束新冠疫情。
在全球抗疫失利的大環境下,為什么中國能在極其嚴峻的病毒遭遇戰中取得勝利?因為我們在嚴格按照科學的規矩做事情。
我們發表這篇論文,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呼吁全球社會回歸理性和科學,而病毒起源的科學探討就是第一步。
《中國科學報》:這篇論文旗幟鮮明地提出:新冠病毒只可能來源于自然界,而不可能從大城市的動物市場里進化出來,更不可能產生于實驗室。你們為什么敢說這樣的話?
吳仲義:我們的文章從兩個方面探討了這個問題。第一,為什么自然界能演化出這樣的病毒?第二,為什么人類造不出這樣的病毒?
要解釋清楚這兩點,就不得不提科學史上經典的“鐘表匠”與“盲眼鐘表匠”的討論。
我們看到,自然界的各種生物都完美地適應著各自的生存環境。1794年,一個英國牧師威廉·佩利提出,自然生物表現出的這種復雜而完美的適應性,就像一塊精巧的鐘表。你無法想象它來自于自然,在這背后一定有一個鐘表匠(造物主)設計并制造了它。
佩利提出這個觀點的時候,達爾文還沒有出生。將近200年后,著名進化論生物學家理查德·道金斯用《盲眼鐘表匠》一書反駁了這一觀點。道金斯強調,物種的演化并沒有特殊的目的。如果大自然是一個鐘表匠的話,只能說它是一位盲眼鐘表匠。一個完美適應環境的物種,不是一下子制造出來的,而是在漫長的歲月里,在大量隨機突變中一步步積累著微小的,但可以提高適應度的改變。
一些人在宣揚“人為論”“陰謀論”“實驗室泄露論”時,一個主要的觀點就是認為像新冠病毒這么完美適應人體的病毒,怎么可能來自于“盲目”的、漫無目的的大自然?這是科學思想上的可怕倒退——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個牧師的思維。
我們想說的是,正因為新冠病毒是人類有史以來見證的最“完美”的病毒,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產物。因為哪怕是最頂尖的人類科學家,當他想要“制造”一個完美適應人群的病毒時,他其實不知道要造什么樣的東西。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術和經驗的電子產品公司,想要一次性設計出一款全球最受歡迎的手機,也是不可能的——最“完美”的產品一定脫胎于市場的檢驗和反復的打磨。
正在開展的一些研究工作也從側面證明了這一點:小鼠原本不能感染新冠病毒,但科學家用人工選擇的方法找到了能夠感染小鼠的新冠毒株。即便如此,這些人為篩選的毒株也無法在小鼠種群中引發如此大規模的疫情。
因此我們推論,在新冠疫情暴發前,相關病毒已經在野生動物和人群中經歷了反復的互相感染,并在這個過程中逐步積累了適應人體的突變。在入侵人間的過程中,病毒屢敗屢戰,直到演化成今天這種極其適應人群傳播的狀態。
與普通感冒相關的人類冠狀病毒(OC43、229E和NL63)的進化史也佐證了這一觀點。這些冠狀病毒在全球傳播之前,已經在人類和野生動物之間相互感染與傳播了數百年。
《中國科學報》:上述推論對開展病毒溯源工作有什么指導意義呢?
吳仲義:病毒溯源必須有一個模型。因為研究人員進行實證調查時,需要知道所搜尋的目標究竟是什么。
打個比方,警察要抓搶劫銀行的嫌疑犯,至少要有一個嫌犯畫像,知道他可能長什么樣子。如果心里沒數,哪怕這個人就坐在你身邊,你都認不出來。
現在很多溯源工作似乎陷入了一個誤區:就是試圖在某種野生動物身上,找到一個跟感染人類的新冠病毒非常相像的毒株。這個邏輯就亂掉了。因為以新冠病毒現在的傳播范圍,如果你找到了這樣一種動物,很大概率是人類傳給它們的,而非它們傳給了人類。
我們需要更具有科學指導意義的理論和模型。
中國的科學家們正在積極提出各種模型和假說。今年我們團隊在《科學通報(Science Bulletin)》上發表了一篇論文:《大流行起源與早期演變的理論探討》。
這篇論文提出了新冠病毒的漸進式演化模型。在此模型中,病毒的PL0(原發地)應當人跡稀少,是動物宿主的棲息地,病毒得以在此處與其動物宿主展開“軍備競賽”。隨后,病毒偶然擴散到了沒有群體免疫的人群中間。第一個疫情暴發地(即PL1),準確來講與PL0有所不同,原因是PL1里的人群對此種病毒沒有免疫力,說明人群事先并沒有接觸過這種病毒。1918年的“西班牙流感”,以及艾滋病的流行,都說明了這種情況的可能性。
與此同時,大量看似互不相關的報道也暗示,可能存在區別于PL1的PL0。
例如,美國2019年12月采集的樣品中檢測到了新冠病毒對應的IgG抗體。而在2019年早些時候,不同地區出現過零散的新冠疑似病例。雖然這些記錄很難一一去證實,但這些報道與我們的猜想是相符的:病毒在從PL0成功入侵到PL1之前,應該已經歷了多次失敗。此前一些新冠病毒與人類的偶然接觸,因為沒有造成大規模嚴重后果,而被忽視了。
《中國科學報》:所以我們現在要找的是PL0(原發地)嗎?該怎么找?
吳仲義:如果要給PL0畫一個像,應該符合如下特征:野生動物數量繁多,特別是存在野生蝙蝠種群;人煙稀少,相對封閉,但少量人口與蝙蝠有較為密切的接觸;當地人口對變異前的新冠病毒具有一定群體免疫力,因此在新冠疫情暴發初期,這些地方可能受影響并不明顯,但是隨著英國變異毒株、德爾塔變異毒株等出現,這些地方的疫情可能會升級。
《中國科學報》:我們能不能拿出科學證據來證明一個地方是PL0(原發地)?
吳仲義:考慮到這些地區的人群很可能已經長期建立對新冠病毒的群體免疫,這個群體免疫的記憶更可能儲存在t細胞里,而非體現在抗體中。這給我們現有的檢測技術帶來了很大挑戰。但我相信,我們早晚能在技術上解決這個問題。
更重要的是,即便證實一個地方就是PL0,這個地方也沒有所謂的“原罪”。新冠病毒的起源是天災而非人禍,人類能選擇的只有如何應對疫情。
《中國科學報》:我們看到,這篇論文的作者名單很長很長。為何這么多著名科學家在用他們的專業背景為這個觀點背書?
吳仲義:我們提出的是一個非常基礎的科學觀點,幾乎所有進化領域的學者都會認同這個觀點:創造“完美”生物的是大自然這個“盲眼鐘表匠”,而不是某個高明的“造物者”。
現在一些人借機攻擊一些研究機構,這是把實驗室當成了“上帝”,本質是非常可笑的。
《中國科學報》:關于病毒溯源問題和這篇論文,您還有哪些想強調的?
吳仲義:病毒溯源是一個嚴肅的科學問題。但現在的狀況是,當我們談論科學時,有些人偏不跟我們談科學。這就像“秀才遇見兵”,根本談不下去。
新冠疫情關乎無數人的生命和健康,關系到全球命運共同體。我們希望在這個問題上,全球社會能盡快回歸科學理性,正視問題,尋找真相。
現在,中國科學家已經拿出了溯源模型,如果誰不信服,也請拿出自己的科學假說,大家一起探討,找到一條通往真相的路!(來源:中國科學報 李晨陽)
相關論文信息:https://doi.org/10.1007/s11427-021-1972-1
四川省醫藥保化品質量管理協會組織召開
2025版《中國藥典》將于2025年10月..關于舉辦四川省藥品生產企業擬新任質量
各相關企業: 新修訂的《中華人..四川省醫藥保化品質量管理協會召開第七
四川省醫藥保化品質量管理協會第七..“兩新聯萬家,黨建助振興”甘孜行活動
為深入貫徹落實省委兩新工委、省市..學習傳達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專題會議
2025年4月22日,協會黨支部組織召..關于收取2025年度會費的通知
各會員單位: 在過去的一年里,..四川省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應急指
四川省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應..四川省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應急指
四川省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應..